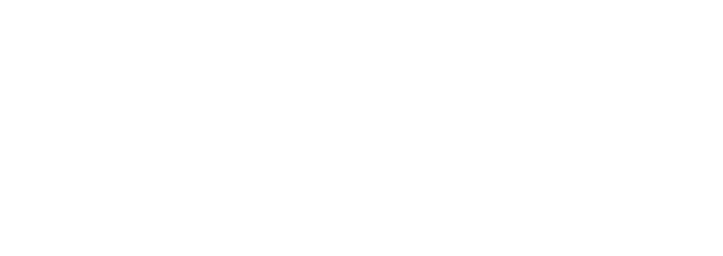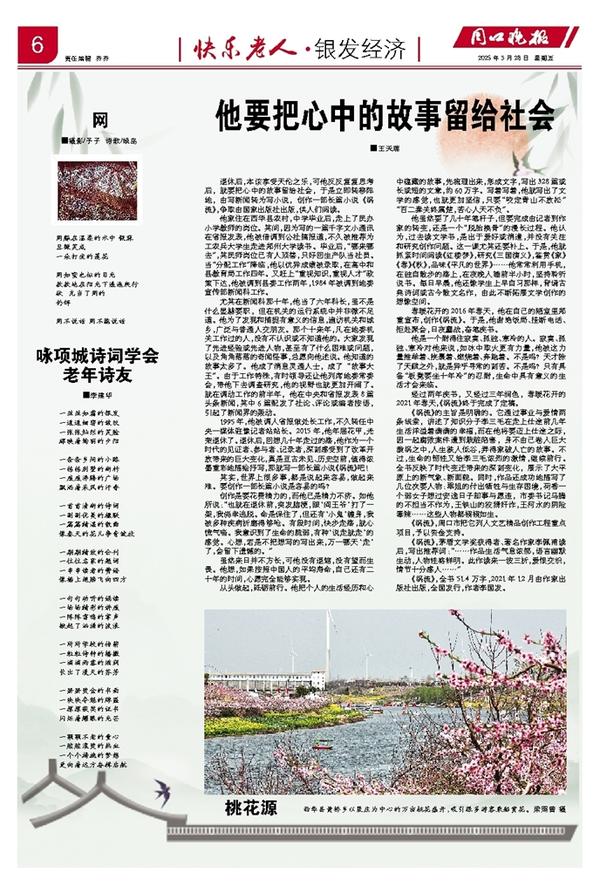他要把心中的故事留給社會
■王天瑞
退休后,本該享受天倫之樂,可他反反復復思考后,就要把心中的故事留給社會,于是立即轉移陣地,由寫新聞轉為寫小說,創作一部長篇小說《渦流》,爭取由國家出版社出版,供人們閱讀。
他家住在西華縣農村,中學畢業后,走上了民辦小學教師的崗位。其間,因為寫的一篇千字文小通訊在省報發表,他被借調到公社搞報道,不久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走進鄭州大學讀書。畢業后,“哪來哪去”,其民師崗位已有人頂替,只好回生產隊當社員。當“分配工作”降臨,他以優異成績被錄取,在高中和縣教育局工作四年。又趕上“重視知識,重視人才”政策下達,他被調到縣委工作兩年,1984年被調到地委宣傳部新聞科工作。
尤其在新聞科那十年,他當了六年科長,雖不是什么顯赫要職,但在機關的運行系統中并非微不足道。他為了發現和捕捉有意義的信息,遍訪機關和城鄉,廣泛與普通人交朋友。那個十來年,凡在地委機關工作過的人,沒有不認識或不知道他的。大家發現了先進經驗或先進人物,甚至有了什么困難或問題,以及角角落落的奇聞怪事,總愿向他述說。他知道的故事太多了。他成了消息靈通人士,成了“故事大王”。由于工作特殊,有時領導還讓他列席地委常委會,帶他下去調查研究,他的視野也就更加開闊了。就在調動工作的前半年,他在中央和省報發表8篇頭條新聞,其中6篇配發了社論、評論或編者按語,引起了新聞界的轟動。
1995年,他被調入省報做處長工作,不久轉任中央一媒體駐豫記者站站長。2015年,他年屆花甲,光榮退休了。退休后,回想幾十年走過的路,他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者、參與者、記錄者,深刻感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,真是亙古未見、歷史空前,值得濃墨重彩地描繪抒寫,那就寫一部長篇小說《渦流》吧!
其實,世界上很多事,都是說起來容易,做起來難。要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是容易的嗎?
創作是要花費精力的,而他已是精力不濟。如他所說:“也就在退休前,突發腦梗,跟‘閻王爺’打了一架,我僥幸逃脫。命是保住了,但還有‘小鬼’纏身,我被多種疾病折磨得夠嗆。有段時間,快步走路,就心慌氣喘。我意識到了生命的脆弱,有種‘說走就走’的感覺。心想,若是不把想寫的寫出來,萬一哪天‘走’了,會留下遺憾的。”
雖然來日并不方長,可他沒有退縮,沒有望而生畏。他想,如果按照中國人的平均壽命,自己還有二十年的時間,心愿完全能夠實現。
從頭做起,砥礪前行。他把個人的生活經歷和心中蘊藏的故事,先梳理出來,形成文字,寫出328篇或長或短的文章,約60萬字。寫著寫著,他就寫出了文學的感覺,也就更加堅信,只要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“百二秦關終屬楚,苦心人天不負”。
他雖然耍了幾十年筆桿子,但要完成由記者到作家的轉變,還是一個“脫胎換骨”的漫長過程。他認為,過去讀文學書,是出于愛好或消遣,并沒有關注和研究創作問題。這一課尤其還要補上。于是,他就抓緊時間閱讀《紅樓夢》,研究《三國演義》,鑒賞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品味《平凡的世界》……他常常利用手機,在獨自散步的路上,在夜晚入睡前半小時,堅持聆聽說書。每日早晨,他還像學生上早自習那樣,背誦古典詩詞或古今散文名作,由此不斷拓展文學創作的想像空間。
春暖花開的2016年春天,他在自己的陋室里鄭重宣布,創作《渦流》。于是,他謝絕飯局、掛斷電話、拒赴聚會,日夜鏖戰,奮筆疾書。
他是一個耐得住寂寞、孤獨、寒冷的人。寂寞、孤獨、寒冷對他來說,如冰中取火更有力量,他被這力量推舉著、挾裹著、燃燒著、奔跑著。不是嗎?天才除了天賦之外,就是異乎尋常的刻苦。不是嗎?只有具備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的忍耐,生命中具有意義的生活才會來臨。
經過兩年疾書,又經過三年潤色,春暖花開的2021年春天,《渦流》終于完成了定稿。
《渦流》的主旨是明確的。它通過事業與愛情兩條線索,講述了知識分子李三毛在走上仕途前幾年生活洋溢著滿滿的幸福,而在他將要邁上仕途之際,因一起腐敗案件遭到栽贓陷害,身不由己卷入巨大漩渦之中,人生跌入低谷,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。不過,生命的韌性又給李三毛濃烈的激情,繼續前行。全書反映了時代變遷帶來的深刻變化,展示了大平原上的新氣象、新面貌。同時,作品還成功地描寫了幾位次要人物:翠姐的付出犧牲與生存困境,荷香一個弱女子想過安逸日子卻事與愿違,市委書記馬騰的不擔當不作為,王鐵山的狡猾奸詐,王河水的陰險毒辣……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。
《渦流》,周口市把它列入文藝精品創作工程重點項目,予以資金支持。
《渦流》,茅盾文學獎獲得者、著名作家李佩甫讀后,寫出推薦詞:“……作品生活氣息濃郁,語言幽默生動,人物性格鮮明。此作讀來一波三折,愛恨交織,情節十分感人……”
《渦流》,全書51.4萬字,202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,全國發行,作者李國發。